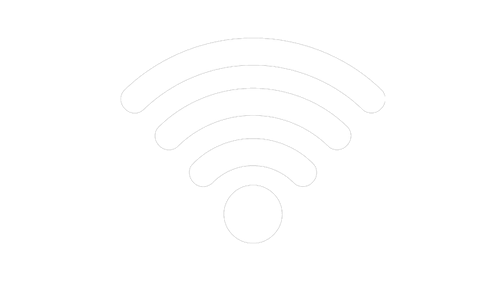按月配资开户 81年刚退伍回家,女知青登门红着脸说:我看上你了
1981年的秋天按月配资开户,我脱下穿了五年的军装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——北方一个叫红松岭的小镇。 火车站还是老样子,青灰色的砖墙上刷着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”的标语,只是颜色褪了不少。站台上的人比五年前多了些,穿着也不再是一片灰蓝,偶尔能看到鲜亮的颜色在人群中闪过。我提着军绿色的行李包,踩在熟悉的石板路上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 五年,足够改变很多东西。 “亮平哥!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。 我抬头,看见弟弟刘亮安挤过人群向我跑来。他长高了,原本稚嫩的脸庞有了青年的棱角,只是那笑...

1981年的秋天按月配资开户,我脱下穿了五年的军装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——北方一个叫红松岭的小镇。
火车站还是老样子,青灰色的砖墙上刷着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”的标语,只是颜色褪了不少。站台上的人比五年前多了些,穿着也不再是一片灰蓝,偶尔能看到鲜亮的颜色在人群中闪过。我提着军绿色的行李包,踩在熟悉的石板路上,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
五年,足够改变很多东西。
“亮平哥!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。
我抬头,看见弟弟刘亮安挤过人群向我跑来。他长高了,原本稚嫩的脸庞有了青年的棱角,只是那笑起来就眯成一条缝的眼睛还和小时候一样。
“亮安!”我放下行李,兄弟俩紧紧拥抱。
“妈在家包饺子呢,韭菜鸡蛋馅儿的,你最爱吃的。”亮安抢过我的行李,“走,回家!”
回家的路上,亮安叽叽喳喳说个不停:镇东头开了家小卖部,能买到上海产的饼干;王大爷家的闺女考上了省城的大学;后山的松林被划成了保护区,不准随便砍柴了……
我安静地听着,目光扫过街道两旁。供销社的招牌换新了,邮局的墙上多了个绿色的邮箱,几个小孩在街角跳皮筋,嘴里唱着我没听过的新歌谣。
展开剩余95%一切既熟悉又陌生。
“对了哥,”亮安突然压低声音,“你知道吗,知青都回城了。”
我点点头。在部队时就听说了政策变化,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。红松岭有个知青点,离镇上三里地,我当兵前那里住着十几个城里来的年轻人。
“咱们镇回来五个,都安排工作了。”亮安继续说,“不过有个女知青,叫李小彤的,她情况特殊……”
“怎么特殊?”我随口问。
“她爸妈都在文革中去世了,城里没亲人了。公社照顾她,让她在镇小学当临时代课老师,住学校旁边的宿舍。”亮安叹了口气,“挺可怜的,一个姑娘家,孤零零的。”
我心里动了一下,但没再多问。
回到家,母亲早已等在门口。五年不见,她的白发多了不少,但精神很好。看见我,她眼圈一红,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:“瘦了,也壮实了。好,回来就好。”
那天晚上,家里的炕头坐满了人。邻居、亲戚、儿时的伙伴都来看我这个“退伍军人”。母亲煮了一大锅饺子,父亲拿出了珍藏的高粱酒,小小的屋子里满是欢声笑语。
“亮平,往后有什么打算?”酒过三巡,隔壁张叔问道。
我放下筷子:“我想去县里农机站学技术。在部队开了几年车,对机械挺感兴趣。”
“好!有想法!”父亲赞许地点头,“现在搞现代化建设,技术人才最吃香。”
正说着,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
离门最近的亮安起身开门,然后愣了一下:“李老师?”
我转过头,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。她大概二十出头,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,两根麻花辫垂在肩上,脸颊被秋风吹得微红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眼睛,大而明亮,像山涧里清凌凌的泉水。
“刘大娘,听说亮平大哥今天回来,我……我来送点东西。”她的声音清脆,带着一点点城里口音,但不难听。
母亲连忙起身:“小彤老师啊,快进来坐!”
姑娘摇摇头,从背后拿出一个布包:“这是我晒的野菊花,泡茶喝清火。还有……我自己纳的鞋垫,听说部队回来的人脚需要放松。”
她把布包递给我母亲,目光却飞快地扫了我一眼。就在那一瞬间,我们的目光相遇了。她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慌忙移开视线,脸颊更红了。
“谢谢李老师,你太客气了。”母亲接过布包,“进来坐会儿吧,正好在吃饭。”
“不了不了,我还有作业要批改。”她摆摆手,转身就要走,又像是想起什么,回头对我说:“欢迎回家,亮平大哥。”
然后她就小跑着离开了,两根麻花辫在身后一甩一甩的。
“这姑娘,总是这么客气。”母亲关上门,把布包放在桌上。
“她就是李小彤?”我问。
“对,小彤老师,人可好了。”母亲打开布包,里面是满满一包金黄色的野菊花,还有两双做工精细的鞋垫,针脚密实整齐,“她在学校教语文和音乐,孩子们都喜欢她。就是命苦,爹妈都没了……”
我拿起一双鞋垫看了看。深蓝色的布面上,用白线绣着简单的云纹,针脚匀称得让人惊讶。一个城里长大的姑娘,竟然有这么好的女红手艺。
“她常来咱家?”我问。
“偶尔来,帮我择个菜什么的。我知道她是孤单,所以常叫她来吃饭。”母亲叹了口气,“多好的姑娘,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。”
那天夜里,我躺在熟悉的炕上,久久不能入睡。五年的军旅生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:新兵连的艰苦训练,边境线上的风雪哨所,退伍前连长拍着我肩膀说“回去好好干”……然后,不知怎么的,那双清泉般的眼睛突然浮现在眼前。
我摇摇头,翻了个身。想什么呢,刚回家第一天。
接下来的日子,我忙着去县里农机站报名,办理各种手续。农机站的领导看了我的退伍证和驾驶经验,很痛快地收下了我,让我先从学徒做起。
白天学技术,晚上回家,生活渐渐步入正轨。偶尔我会在镇上的小路上遇见李小彤,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,看到我时轻轻点个头,脸微微一红,就快步离开了。
直到那个星期六的下午。
我正在后院修父亲那辆老旧的自行车,母亲在厨房里喊:“亮平,去供销社打瓶酱油,顺便买斤盐。”
我洗了手,拿起玻璃瓶就往供销社走。秋天的阳光暖洋洋的,路边的杨树叶开始泛黄,风一吹,哗啦啦地响。
供销社里人不多,我打完酱油正要离开,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:“请问有红色毛线吗?”
是李小彤。她站在柜台前,微微踮着脚看货架上的东西。
售货员拿出几团毛线:“就剩这些了,上海产的,质量好。”
李小彤仔细地比较着颜色,侧脸在从窗户透进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柔和。她今天穿了件浅粉色的衬衫,外面套着米色开衫,比第一次见面时那身工装多了几分女孩子的秀气。
选了好一会儿,她终于挑中一团:“就要这个吧。”
付钱时,她翻遍了口袋,脸渐渐涨红:“对不起,我……我钱不够,差一毛钱。”
售货员的脸拉了下来:“差一毛?那不行,我们这儿不赊账。”
“我明天补上行吗?今天急着用……”李小彤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“规定就是规定。”售货员伸手要收回毛线。
“等等。”我走过去,从兜里掏出一毛钱放在柜台上,“差多少?我这儿有。”
李小彤猛地抬头,看见是我,眼睛一下子瞪大了:“亮平大哥?不,不用,我……”
“拿着吧。”我对售货员说,“毛线给她包好。”
走出供销社,李小彤抱着那团红色毛线,跟在我身后,像个犯错的孩子。
“谢谢你,亮平大哥。我明天一定还你钱。”她小声说。
我笑了:“一毛钱的事,别放在心上。你要织什么?”
“围巾。”她的声音大了些,“天快冷了,想给班上的孩子们织几条。有些孩子家里困难,冬天连条围巾都没有。”
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她。她自己过得也不容易,却想着别人。
“你……你挺会照顾人的。”我说。
她摇摇头,脸上又浮现出那种害羞的红晕:“我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那些孩子对我很好,知道我孤身一人,常从家里带吃的给我。”
我们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。秋风拂过,路边的蒲公英飞舞起来,像小小的降落伞。
“你在农机站学得怎么样?”她突然问。
“还行,师傅人不错,肯教。”我说,“你呢?在学校还习惯吗?”
“习惯。孩子们单纯,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。”她顿了顿,“就是有时候……有点想家。虽然家里已经没人了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。五年军旅,我知道想家的滋味,但至少我知道家里有人等我。而她,是真的无家可想了。
“红松岭就是你的家。”最后我说,“这里的人都很朴实,会把你当自己人的。”
她抬头看我,眼睛亮晶晶的:“嗯,我知道。刘大娘对我就特别好。”
走到小学门口,她停下脚步:“我到了。谢谢你,亮平大哥。”
“叫我亮平就行。”我说,“大哥大哥的,听着生分。”
她笑了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,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:“好,亮平。那你叫我小彤。”
“小彤。”我试着叫了一声。
她的脸又红了,抱着毛线跑进了校门。
那天晚上,我在灯下看书,眼前却总是浮现出她笑时的梨涡。我甩甩头,继续看我的《农机维修手册》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和小彤渐渐熟悉起来。她偶尔会来我家,帮母亲做些针线活。母亲喜欢她,说她手巧心细。小彤做的饭菜也很好吃,虽然都是简单的家常菜,但有种特别的味道。
十月底的一个星期天,父亲让我去后山捡些柴火。我拿着绳子和砍刀上了山。秋天的山林色彩斑斓,枫叶红得像火,松树绿得深沉,地上铺满了金黄的落叶。
我正在捆拾到的枯枝,突然听见有人哼歌。循声望去,看见小彤坐在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上,手里拿着本子写着什么。
“小彤?”我走过去。
她吓了一跳,手里的笔差点掉地上:“亮平?你怎么在这儿?”
“捡柴火。你呢?”
“我来写生。”她合上本子,但没完全合拢,我瞥见里面是些素描,画的是山里的树木和石头。
“你会画画?”我惊讶地问。
“以前学过一点。”她有些不好意思,“妈妈是美术老师,她教我的。现在偶尔画一画,怕手生了。”
我在她旁边的石头上坐下:“能看看吗?”
她犹豫了一下,把本子递给我。
我翻看着,里面的画虽然简单,但很有灵气。一棵歪脖子松树,几块形态各异的石头,甚至还有一只站在枝头的小鸟,都栩栩如生。
“画得真好。”我由衷地说。
“谢谢。”她接过本子,低头抚平边角,“画画的时候,我能感觉到妈妈还在身边。”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,只有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。
“亮平,你在部队的时候,想过家吗?”她突然问。
“想,天天想。”我说,“特别是过节的时候。部队的饺子再好吃,也比不上家里的味道。”
“我爸爸妈妈是在我下乡那年走的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像在自言自语,“车祸。邻居写信告诉我时,我已经在红松岭了。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”
我的心揪紧了。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,但无法想象她当时的感受——一个人在农村,突然成了孤儿。
“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。”她继续说,“是村里的老乡们安慰我,照顾我。特别是刘大娘,她常来看我,给我送吃的,就像……就像妈妈一样。”
“我妈是个热心肠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,抬起头时眼睛有点红,但她在微笑,“所以我觉得,红松岭是我的第二个家。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了,但我在这里找到了家人。”
那天我们聊了很久,从日头正午聊到夕阳西下。我给她讲部队里的趣事,她给我讲学校孩子们的童言稚语。下山时,我背着一大捆柴,她走在我旁边,手里拿着一把野菊花。
“亮平,你有想过以后吗?”她问。
“以后?好好学技术,争取转正,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”我说。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……”我顿了顿,“娶个媳妇,成个家。”
说完这话,我突然觉得脸上发热。偷偷看她,发现她的耳根也红了。
深秋的一天,农机站派我去县里送零件。回来时天已经擦黑,我刚进镇子,就看见小学方向围了一群人。
我心里一紧,快步跑过去。只见小彤的宿舍门口,几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正在嚷嚷什么。小彤站在门内,脸色苍白。
“怎么回事?”我挤进人群问邻居王大妈。
“这几个是镇上的二流子,喝多了酒,听说小彤老师一个人住,就跑来胡闹。”王大妈愤愤地说。
我二话不说,走上前去:“你们干什么?”
为首的一个高个子青年斜眼看我:“你谁啊?少管闲事。”
“我是刘亮平,退伍军人。”我站直身体,五年的军旅生涯让我比这些瘦弱的青年壮实不少,“识相的赶紧走,不然我去派出所叫人。”
“退伍军人了不起啊?”另一个青年嘴上硬气,脚步却在后退。
“试试看?”我向前一步。
几个人互相看了看,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围观的人群散去,我走到门口:“小彤,你没事吧?”
她摇摇头,但手在发抖:“没事,谢谢你。”
“以后晚上锁好门。再有这种事,大声喊,邻居们都能听见。”我说。
“嗯。”她轻轻应了一声,突然问:“你吃饭了吗?”
“还没。”
“我做了疙瘩汤,要不要……吃点?”她问得很小心,眼睛里有一丝期待。
我本来想拒绝,但看到她苍白的脸,改了口:“好。”
她的宿舍很小,一张床,一张桌子,一个书架,但收拾得很整洁。墙上贴着她画的画,窗台上摆着一排野花。
疙瘩汤热气腾腾,里面加了白菜和土豆,简单却香。我们面对面坐着,安静地吃饭。
“今天谢谢你。”她又说了一遍。
“别客气。以后有事就叫我,我家离这儿不远。”我说。
她点点头,然后轻声说:“亮平,其实我……”
话没说完,外面传来敲门声。是亮安:“哥,妈叫你回家吃饭!”
我起身:“那我先走了。你早点休息,锁好门。”
走出宿舍,冷风一吹,我才意识到刚才屋里有多温暖。亮安跟在我身边,挤眉弄眼:“哥,你在小彤老师那儿吃饭?”
“嗯,怎么了?”
“没什么。”亮安笑得贼兮兮的,“妈说了,小彤老师是个好姑娘。”
我拍了下他的后脑勺:“别胡说。”
但那天夜里,我失眠了。眼前总是浮现出小彤苍白的脸,和她未说完的话。
冬天来了,红松岭下了第一场雪。整个世界银装素裹,美得像画。农机站的工作进入淡季,我有更多时间在家。
小彤来我家的次数更多了。有时是帮母亲做棉衣,有时是来烤火取暖。她和我家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,连严肃的父亲看到她都会露出笑容。
冬至那天,小彤来家里包饺子。母亲和面,她调馅儿,我擀皮儿,三个人围着桌子忙活。
“小彤调馅儿有一手,比你妈我还强。”母亲夸赞道。
“大娘别这么说,我就是按我妈教的方法做的。”小彤不好意思地说。
“你妈妈一定是个能干人。”母亲说。
小彤的眼神暗了暗:“嗯,她很能干,什么都会。”
我赶紧岔开话题:“听说学校要办元旦晚会?”
“对,孩子们在排练节目。”小彤的眼睛又亮起来,“我教他们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还有几个孩子在排小品,可有趣了。”
“到时候我们能去看吗?”母亲问。
“当然能,欢迎大家都来。”
饺子煮好了,热腾腾的端上桌。父亲倒了点酒,我们举杯庆祝。
“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!”父亲说。
“愿大家都平安健康!”母亲说。
“愿……”小彤看了我一眼,脸微微红了,“愿一切都好。”
吃完饭,小彤要回学校。母亲让我送她。
雪已经停了,月光照在雪地上,泛着淡淡的蓝光。我们踩在雪上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
“亮平,过了年我就二十三了。”小彤突然说。
“嗯,我二十六。”我说。
“你……你有对象吗?”她问得很轻,几乎被踩雪声盖过。
我心跳漏了一拍:“没,在部队没时间,回来又忙。”
“哦。”她应了一声,不再说话。
快到学校时,她停下脚步:“亮平,我……我有话想跟你说。”
“你说。”
她深吸一口气,抬起头看着我,月光下她的眼睛像含着一汪水:“我……我看上你了。”
时间仿佛静止了。我只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,咚咚咚,像敲鼓一样。
“从第一次见到你,我就觉得你不一样。”她的声音在颤抖,但坚持说下去,“你正直,善良,有责任心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,我没父母,没背景,只是个临时代课老师,可能哪天就失业了。但我……我就是喜欢你。”
雪花又开始飘落,一片落在她的睫毛上,她眨眨眼,雪花化了,像一滴泪。
“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,就当我没说。”她低下头,“我们还是朋友。”
我看着眼前这个姑娘,这个勇敢又脆弱的姑娘。我想起她害羞的笑容,想起她为孩子们织围巾,想起她一个人在山上画画,想起她调的美味的饺子馅。
我的心突然变得很柔软。
“小彤。”我开口,声音有点哑。
她抬头看我,眼睛里满是紧张和期待。
“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”我深吸一口气,“我也看上你了。”
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。
“你善良,坚强,有才华。”我继续说,“你一个人面对那么多困难,却还是那么乐观,那么为别人着想。这样的姑娘,我怎么会觉得不合适?”
雪花在我们之间飞舞,她的脸在月光和雪光中,美得不真实。
“真的?”她的声音哽咽了。
“真的。”我用力点头。
她笑了,眼泪却流下来。我伸手,轻轻擦去她的泪水。她的手很凉,我握住,放进我的大衣口袋。
“手这么凉,明天我给你做个手炉。”我说。
“你会做手炉?”
“在部队跟战友学的,用铁皮罐头改就行。”
我们相视而笑。那一刻,所有的犹豫和不安都消失了,只剩下满满的甜蜜。
从那天起,我们的关系变了。我们还是会在路上相遇,但她不再害羞地低头走过,而是会停下来,对我笑。我还是会送她回学校,但不再是一前一后,而是并肩而行。
元旦晚会那天,我和家人都去了学校。小彤的班级表演了合唱,孩子们稚嫩的歌声让全场动容。晚会结束后,小彤被孩子们围住,她笑着,眼里有光。
“小彤老师真受欢迎。”母亲感慨。
“她是个好老师。”父亲难得地夸人。
回家的路上,母亲试探地问:“亮平,你和小彤……”
“我们在谈对象。”我坦然承认。
母亲笑了:“好,好。小彤是个好姑娘,你要好好待她。”
“我会的。”
冬天最冷的时候,小彤的宿舍炉子坏了。我连夜给她修好,又检查了烟囱,确保不会漏烟。她给我倒了热水,我们围着炉子说话。
“亮平,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教书了,怎么办?”她忧心忡忡地问。
“那就做别的。你会画画,可以给书本画插图;你会做饭,可以开个小吃店;你还会织毛衣,现在机器织的毛衣都不如手织的暖和。”我一一列举,“你有这么多本事,怕什么?”
她笑了:“在你眼里,我好像什么都会。”
“你本来就什么都会。”我说。
炉火映着她的脸,红扑扑的。我握住她的手:“小彤,不管发生什么,我们一起面对。”
她靠在我肩上:“嗯,一起。”
春节到了,这是小彤在红松岭过的第三个春节,但却是第一个有“家”的春节。母亲坚持让她来家里过年,说她一个人太冷清。
年夜饭很丰盛,鸡鸭鱼肉样样俱全。小彤做了她的拿手菜——糖醋排骨,被一扫而光。父亲给她包了个红包,她推辞不要。
“拿着,孩子。”父亲说,“在我们家,你就是自家闺女。”
小彤的眼圈红了。
吃完饭,我们一起守岁。亮安嚷嚷着要打扑克,我们四人玩升级,小彤和我一家。她打牌很聪明,我们赢多输少。
十二点的钟声响起,外面响起鞭炮声。我们走到院子里,看漫天烟花。
“新年快乐!”大家互相拜年。
我悄悄握住小彤的手:“新年快乐,小彤。”
“新年快乐,亮平。”她仰头看我,烟花在她眼中绽放。
那一刻,我知道,这就是我要守护的人,这就是我的未来。
春节后,我去小彤宿舍的次数更多了。有时是给她带母亲做的吃的,有时是帮她修修补补。她的宿舍渐渐有了我的痕迹:窗台上多了一盆我送的仙人掌,墙上挂了我从县里买的年历,桌上放着我给她做的手炉。
三月初,冰雪开始消融。一个周末,我约小彤去河边散步。河面的冰已经裂开,河水潺潺流淌,带着碎冰向东流去。
“春天要来了。”小彤说。
“嗯,新的一年开始了。”我看着她,“小彤,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
“什么事?”
“我想去考农机站的正式编制。”我说,“如果考上了,就是正式工,待遇会好很多。但需要去市里培训三个月。”
小彤的眼睛亮起来:“这是好事啊!你去考,一定行的。”
“可是要去三个月……”我有些犹豫。
“三个月很快的。”她笑了,“我等你。”
我握住她的手:“那说好了,你等我。”
“嗯,说好了。”
四月份,我通过了农机站的考试,获得了去市里培训的机会。临走前一天,小彤来送我。她织了一条灰色的围巾给我:“市里风大,戴着暖和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织的?我都不知道。”
“晚上批改完作业织的。”她帮我围上,“要按时吃饭,别熬夜学习。”
“你也是,别太累。”
第二天,我坐上了去市里的班车。小彤站在车站,一直挥手,直到车拐弯看不见。
市里的培训生活很紧张,白天上课,晚上自习。但我每周都给小彤写信,告诉她市里的新鲜事,问她学校的情况。她的回信总是很及时,字迹娟秀,内容温暖。
培训进行到第二个月时,我在信里写:“市里的公园花都开了,可惜你不能来看。下次,我们一起来。”
她回信:“好,一起去。学校后面的山坡上,野花也开了,我画了几幅,等你回来看。”
六月底,培训结束,我以优异成绩结业,成为农机站的正式技术员。坐上回红松岭的班车,我的心早已飞回家。
车到站时,我一眼就看见小彤在站台上。三个月不见,她好像瘦了点,但笑容更加灿烂。
“欢迎回家!”她跑过来。
“我回来了。”我张开手臂,拥抱了她。周围有人看,但我们不在乎。
回家的路上,我告诉她培训的趣事,她告诉我学校的新闻。走到小学门口时,她突然说:“亮平,我也有个好消息。”
“什么?”
“公社决定,让我转正了。”她的眼睛闪闪发光,“从下学期开始,我就是红松岭小学的正式教师了。”
“太好了!”我高兴地抱起她转了一圈。
她惊呼一声,然后笑起来,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。
那个夏天,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。我常去学校接她下班,我们一起散步,一起去后山写生,一起在河边看夕阳。
八月的一个傍晚,我们坐在河边。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,微风拂过,带来野花的香气。
“小彤。”我轻声叫她。
“嗯?”
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她愣住了,转过头看我:“你说什么?”
“我说,我们结婚吧。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,打开,里面是一枚银戒指,是我用第一个月正式工资买的,“嫁给我,好吗?”
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,但她在笑:“好。”
我把戒指戴在她手上,大小正合适。她看着戒指,又看看我,突然扑进我怀里。
“亮平,我会做个好妻子的。”她哽咽着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我轻抚她的背,“我也会做个好丈夫。”
我们的婚礼定在十月一日,国庆节。母亲说这是个好日子,举国同庆。
婚礼很简单,但很温馨。我们在镇上办了酒席,请了亲戚朋友和学校的同事。小彤穿了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,我穿着军装改的西装。我们向毛主席像鞠躬,向来宾敬酒。
父亲在婚礼上说:“亮平,小彤,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夫妻了。要互敬互爱,互相扶持,把日子过好。”
“我们一定。”我握着小彤的手,郑重承诺。
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。我们住在农机站分的一间小平房里,虽然不大,但被小彤布置得很温馨。她教书,我修农机,下班后我们一起做饭,一起散步,一起规划未来。
第二年春天,小彤怀孕了。我们激动得一晚上没睡,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,是男孩还是女孩。
“要是女孩,就叫她刘思彤,思念的思,你的彤。”我说。
“要是男孩呢?”
“刘建国,建设国家的建国。”
小彤笑了:“都听你的。”
十月怀胎,小彤生了个女儿。粉嘟嘟的小脸,眼睛像小彤,又大又亮。我们给她取名刘思彤,小名彤彤。
抱着女儿,小彤哭了:“亮平,我们有家了,完整的家。”
我搂住她:“对,完整的家。”
时光飞逝,转眼到了1985年。我们的女儿彤彤三岁了,聪明可爱。小彤依然是红松岭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,我成了农机站的技术骨干。生活虽然不富裕,但充满希望。
一个秋日的傍晚,我们一家三口在河边散步。彤彤在前面跑,捡地上的落叶。
“妈妈,你看,这片叶子像蝴蝶!”她举着一片枫叶跑回来。
“真像。”小彤接过叶子,夹在随身带的本子里。
我牵着小彤的手,看着女儿欢快的身影,心里满是感激。
“亮平,还记得吗?四年前,也是这样的秋天,我在这里跟你说……”小彤的脸红了。
“说你看上我了。”我接话。
“嗯。”她靠在我肩上,“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的事。”
“也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话。”我亲了亲她的额头。
夕阳西下,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彤彤跑回来,一手拉着我,一手拉着小彤:“爸爸妈妈,回家啦!”
“好,回家。”我们异口同声。
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这四年来的点点滴滴。从那个害羞的女知青,到现在的妻子和母亲,小彤用她的善良和坚强,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喜爱。而我,从一个刚退伍的愣头青,成长为丈夫和父亲,懂得了责任和担当。
命运让我们在1981年的秋天相遇,从此,两颗孤独的心有了依靠,两个漂泊的人有了归宿。
这或许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——在平凡的日子里相守,在岁月的长河中相伴,直到白头。
夜色渐浓,家里的灯亮了,温暖的光透过窗户,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。小彤的手在我手心,温暖而坚定。我知道,无论未来还有多少风雨,我们都会携手走过。
因为从她说“我看上你了”的那一刻起按月配资开户,我们的故事,就注定要写一辈子。
发布于:陕西省